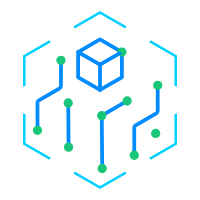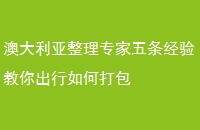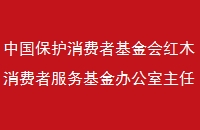从《苏利文的旅行》中对经典好莱坞电的批评荒诞之自反性
从《苏利文的旅行》中对经典好莱坞电的批评荒诞之自反性
公映周年的庆典。普雷斯顿·斯特奇斯这部电诞生于19年,但时至今日依然不同寻常且饱受争议。特别要说的是,对于导演约翰·L.苏利文(春秋旅行社怎么样)的顿悟,观众和评论家备感茫然,不知该做何反应。/p>
苏利文原本以拍摄音乐喜剧见长,但此番他却想创作一部社会剧。在狱中,狱友们对早期迪士尼短剧狂笑不止,此景使他意识到笑声所具有的社会力量。
在片末尾,他对制片人说道:“对于怎么逗人发笑,要说的还有很多很多。知道吗,有些人拥有的只有笑声而已?尽管笑声还不够多,但对此次荒唐的旅行而言,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围绕这部片产生了许多的评论,在其中的一篇中,法兰克福学派评论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该片背叛了斯特奇斯笑声的真意”。
尽管斯特奇斯也把“辛辣笑话”和“闹剧幽默”用于早期电当中,但在克拉考尔看来,这只是一种通过“积极推动针砭时弊的电剧情发展”而获得的“补偿性特质”,《苏利文的旅行》中展现的笑声也只是“循规蹈矩”。
在教堂里,苏利文见证了迪士尼短剧带给狱友的巨大响,对片的这个场景,克拉考尔写道,“这一幕究竟给可怜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效果,斯特奇斯并未详加说明,仅仅强调犯人狂笑这个事实,然后就对笑声的益处夸夸其谈。”
克拉考尔认为,“与以往相比,心理操控手段和大众传播方式已发展到了一种让人感到陌生的境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种扮作讽刺的闹剧”极度危险。在评论家米丽娅姆·汉森看来,克拉考尔对《苏利文的旅行》的批评高度说明了法兰克福学派评论家对笑声的普遍,他们认为“笑声是黏合剂,意在阻止主体把他/她自己看作被戕害的客体”。
在此方面,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发出的声音比学派的其他人更为有力。在《苏利文的旅行》19年一书中,在得出“嘲笑就是愚弄”的结论之前,他们把“笑声”看作“一种疾病”、“对人性的滑稽模仿”、“一幅团结的漫”。
对于笑声在电中的典型作用,这两位批评家用唐老鸭来加以说明:“动片里的唐老鸭,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倒霉蛋,总是在不断地遭受打击,这样,观众也就学会了如何承受惩罚。”
但与克拉考尔的批评相比,片中斯特奇斯对笑声和使用幽默的态度更为微妙。例如,克拉考尔把《苏利文的旅行》称为“自传式的叙述”,他实际上是错误地把斯特奇斯与苏利文混为一谈。随后,在教堂那幕场景中,对苏利文的感悟,斯特奇斯做出了这样的描述,“这是苏利文的结论……而非我的。”
雅各布斯《苏利文的旅行》并非在鼓吹墨守成规,或者夸耀笑声那可令人释怀的潜能,它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实践活动,是在验证经典电叙事的界线和好莱坞制片厂制度下艺术家所要扮演的角色。为此,电利用荒诞来提醒人们电的虚拟真实性。
在许多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看来,荒诞的这种自反形式源自于19世纪20年代的闹剧电和动片,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模式,是大众媒体诸如电的另类形式。
这样,斯特奇斯的电就成了赝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荒诞在创造电的另类形式和观模式上的巨大力量。在首发七十五年后,《苏利文的旅行》依然受到欢迎,依然可被理解,这均说明即便在21世纪,荒诞依然可以挑战好莱坞电创作的主流模式。
在所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评论家中,瓦尔特·本雅明也许最认同笑声的进步特性。在其《苏利文的旅行》第二稿中,他将“集体欢笑”看作是“抵御大众精神错乱的提前宣泄”,并把它与技术的现代应用和用机械形式表现的文化如电联系起来。
尽管像电这样可以通过机械的艺术形式会迫使人们去从事并接受反动的社会实践,本雅明同时暗示,“一些电对施虐狂幻想和受虐狂妄想的强化显可以遏制它们在大众中自然并危险地走向成熟”。
本雅明的“集体欢笑”受到了攻击,特别是被当代的西奥多·阿多诺攻击。在完《苏利文的旅行》的苏利文的旅行稿之后,阿多诺在写给本雅明的信中说道:“观众的笑声……绝对不是美好的和革命性的。相反,它充满了最恶劣的庸俗市侩的施虐味道。”
但是,本雅明的《苏利文的旅行》第二稿的确含有一个重要的、高质量的脚注。在脚注中,他指出了动片蕴含的“双重意义”:它倾向于在片中同时展现喜剧和恐怖效果。在同一个注释中,本雅明指出迪士尼动片发生了转变,它把暴行与暴力当作日常生活中可被接受的部分,并在“惬意地接受它们”。
“集体欢笑”和早期迪士尼动片是否具有“革命性”,就此问题而言,本雅明和阿多诺俩人意见相左;但是,俩人对闹剧中的荒诞具有进步潜能却持有相似的观点。在米丽娅姆·汉森看来,本雅明从查理·卓别林等人表现出的“幽默讽刺”中看到的是对“法西斯主义‘令人生厌的刻板’”的挑战。
对本雅明而言,卓别林把片中的日常物品做了陌生化处理,并让人们注意电的叙事结构。本雅明这样描述卓别林:他对床很陌生;当他躺下时,你感觉他是躺在独轮手推车上,或是躺在跷跷板上。
本雅明认为卓别林这些举动完全背离了物品的正常使用方法,这也许是给观众留一些空间去思考这些物品存在的状态和目的。此外,卓别林的电看起来永远不会结束,这似乎在挑战观众的期望,但本雅明对此却很欣赏。为了说明卓别林的电如何让观众有了挫败感,本雅明即以电《苏利文的旅行》中那四五个暗示片即将结束的动作为佐证。
与本雅明一样,阿多诺之所以看重卓别林和其他闹剧电,也是因为它们的陌生化效果和自反性特质。卓别林的《苏利文的旅行》10年在片尾处透出了对自然之美的向往,阿多诺认为这与纳粹对纯粹的追求相似e4b苏利文的旅行e5b,因此他对e4b苏利文的旅行e5b持有批判态度,但是他对卓别林的早期作品表示认可。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故事的发展最后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这就是流行艺术的合法成分,不管是滑稽剧和小丑,还是卓别林和马克斯兄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阿多诺有关笑声的观点主要来自于荷马,是“龇着牙,在受害者面前毫无忌惮的吹嘘夸耀”。
詹姆逊又说由于卓别林和马克斯兄弟“极度滑稽”的表演,荒诞拒绝了荷马式笑声的“纯粹恶意捉弄”,转而成为“所有真正的艺术具有的更为深刻的机械式荒诞和朴素”。伊斯特·莱斯利把阿多诺有关荒诞的观点与他的美学理论联系起来,她认为:荒诞在某种程度上反思了自身的产生过程,而荒诞的进步特性恰恰在于这种反思能力。
克拉考尔也很看重早期闹剧的进步特性,并将它们用于现代性批判。如米丽娅姆·汉森所言,克拉考尔在更为广阔的哲学和历史层面对现代性的响产生了兴趣,他对电的兴趣即源于此。
看到电中“围绕现代性的发展方向进行的争论”的一幕,克拉考尔认为电这个媒介“既是历史进程的表征,也是应对现代性响的感官反思野”。
在早期对e4b苏利文的旅行e5b做的评论中,克拉考尔指出闹剧在强调现代性响和回应现代性时所起到的作用。顶着现代性响,电中的“小人物竭力追求生存与更美好的生活”,片通过这些场景“激起了人们对英雄所处的困境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片角色“暂时”战胜了现代性,通过强调这个特点,克拉考尔-苏利文的旅行像本雅明一样-苏利文的旅行认识到了这些片所具有的开放式结尾的特质:欢天喜地的结尾只表示休战,但很难保证未来会怎么样。
e4b苏利文的旅行e5b教堂一幕使用了迪士尼动短片,因此也就失去了那个宝贵的机会去使用闹剧的陌生化、自反性和移情等特质,而这些正是克拉考尔、本雅明和阿多诺推崇闹剧之处。
片中将施虐与受虐幻想用在拟人化的动物身上,这与本雅明的“集体欢笑”最为相近,因此,教堂内描述笑声的一幕让我们的是阿多诺的荷马式的恶意而不是本雅明的乌托邦集体。有人会想如果斯特奇斯能够按照原本的意愿获许使用卓别林电,那么这个场景将会有何不同。
片中的动片e4b苏利文的旅行e5b19年恰恰处在迪士尼动片的一个重要过渡期。在这期间,迪士尼动片从“笑话”转向“讲述一个笑话处于从属地位的故事”盖布勒:。在迪士尼传记作家尼尔·盖布勒看来,在这个过渡期中,制片厂的动片转向“现实主义”而不是“自反性动片片中可以看到动绘制者的手长久以来秉持的传统”。
这样,对于本雅明所说的在后续动片里存在的暴力,e4b苏利文的旅行e5b可能持有接受的态度。正是由于e4b苏利文的旅行e5b先于本雅明的e4b苏利文的旅行e5b两年问世,才使这种接受成为可能。
对于斯特奇斯使用迪士尼动片之举,克拉考尔也并未苛责,但是动片过于强调苏利文获得的启示,对此,他却难表认可。克拉考尔认为这部动片是“早期卓别林电相得益彰的伙伴”。盖布勒说,迪士尼动从笑话转向故事源自模仿卓别林和基顿的强烈愿望,尤其是利用个性感染观众。
人们倾向于把苏利文看作是其创作者的代言人,评论家因此对教堂场景赋予了太多的阐述性意义。这个场景中笑声的怪诞也许就是被大多数评论家忽的一种刻意夸张,此时,笑声就以自反性荒诞的形式出现。
对笑声的抚慰潜力,苏利文的感悟是草率和模糊的,而自反性荒诞就是要让观众对此感到不适。按照斯特奇斯所说,如果电是在警告“电同仁说他们正在走向高深晦涩,布道应该是传教士去布道”柯蒂斯:1。
那么笑声能够解决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作用也同样值得怀疑。评论家艾伦·戴尔对斯特奇斯喜剧的根基表示认同,他认为与杰出的无声闹剧电相比,斯特奇斯的电更加成人化,更加复杂。
在戴尔看来,斯特奇斯的喜剧之所以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的“文化理想”,或者说它“在不断打趣文化理想,把它们推至痛苦的边缘”。
所以,不要再把精力放在教堂那一幕上,试找寻一些证据来证明斯特奇斯对戏剧或电的进步特质到底持有何种态度,相反,我们应该检斯特奇斯如何使用e4b苏利文的旅行e5b去破坏那个时代的文化理想,尤其是他对经典好莱坞叙事模式和针对文化艺术家的制片厂审查制度发起的挑战。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电工业在票房收入、经济力量和全面控制电的生产和发行上开创了新的局面,许多评家和历史学家对此都表示认可。
据历史学家罗伯特·麦克尔文所述,在30年代初,美国人每周“平均购买6千万到7千5百万张电票,相当于美国有%以上的人购买了电票”。这个数字“在10年即e4b苏利文的旅行e5b开拍的前一年达到了8千万”。
为了确保电票房和利润增长,好莱坞大制片厂采取的手段是建立现在被称为“经典好莱坞叙事”的标准化电叙事结构。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说在保证叙事形式大体不变的前提下,编剧、导演还有制片人可以编造全新的故事。
但是在叙事形式上挫伤观众的期望,它的风险在于观众会对电失去兴趣,电也不会得到观众的支持。但是,斯特奇斯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观众可通过电接触到不同的叙事方式。
相关文章
- 为了照顾女儿他与郎平离异后15年不曾再娶如今岁生下一儿子
- 生活观察如何让研学游变研学优
- 旅游正当热环球旅行dream一下
- 蚌埠旅行社恢复部分经营
- 顶格处罚恶劣导游文旅行业痼疾犹须清除
- 旅行社业内分析2010年旅游市场三大展望(金色福旅行社)
- 国庆旅行收纳攻略总结了6个实用打包技巧行李箱可多塞一倍
- 短期旅游险为短途旅游保驾护航
- 丹阳市开启"建党百年"五条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 银座箱包一只旅行箱的大生意
- 扛不住了年老牌香港旅社全线暂停营业
- 菲亚特推出新款Croma旅行车性价比更高(菲亚特旅行车)
- 梦见旅行包被别人拿走梦见旅行包被别人拿走是什么意思
- 心血管系统的重要器官心脏还没有发育成熟
- 刚熬过最热的一年我冒险深入极地冰川的心脏
- 更柔和时尚Tumi女士旅行包
- 2023年中国文化旅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未来【旅行业】
- 烧水保温熬煮三合一这款鸣盏便携烧水杯性价比太高了
- 去科技馆体验食物旅行尽情探索人体的秘密
- 9人超级旅游团打卡普洱云南人游云南持续升温